
一周前,硅谷爆出消息:Meta以4年2億美元的天價合約,從蘋果挖走AI模型團隊負責人龐若明,并組建超級智能實驗室,誓要在AI競賽中翻盤。然而,聲勢浩大的人才爭奪戰背后,卻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現實——Meta,這家曾經的社交媒體霸主,在AI的路上,可以說節節落敗。
Llama 4模型表現不及預期,被開發者質疑特調作弊;Behemoth大模型跳票,內部測試結果慘淡;為AI研發提供現金流的廣告業務遭遇70億美元縮水,Temu和Shein因特朗普關稅政策大幅削減預算……
Meta的AI之路,為何越走越窄?扎克伯格的百億美元豪賭,究竟是Meta的絕地反擊,還是另一場預示失敗的轉型?

作為社交媒體時代的絕對霸主,Meta曾經坐擁著業內最頂級的資源。研究團隊有著楊立昆這樣的頂級科學家坐鎮,資金上憑借廣告業務每年千億美元的現金流支撐。
但讓人疑惑的是,它如何步步落敗到了如今不得不重金搶人的局面?我們一起來回溯一下。
Meta曾引領2010年的AI研究,推出PyTorch等主流研究工具。然而,與谷歌TensorFlow和微軟Azure AI不同,Meta研究長期停留在學術導向,錯失了技術商業化的先機。

2022年,生成式AI興起的前夜,比OpenAI早三月推出聊天機器人的Meta本有可能最先成為拿起火把的人。可惜,BlenderBot 3和Galactica因頻繁輸出虛假信息黯然下架。同期,楊立昆對大語言模型的公開質疑進一步加劇戰略搖擺,讓其錯失ChatGPT風口。
2023—2024年,在其他公司都全力沖刺大模型時,扎克伯格的All in元宇宙戰略分散了資源,導致算力布局落后。
前期失利累積的矛盾,在2025年全面爆發。Llama 4表現不佳,被開發者質疑“特調作弊”,核心人才流失;Behemoth大模型跳票,內部測試結果慘淡,被曝或將放棄;商業化上,Meta的AI應用日活僅45萬,與其社交平臺20億日活的龐大體量形成鮮明對比,遠低于ChatGPT;禍不單行,特朗普政府對華加征關稅導致Temu、Shein等主要廣告客戶大幅削減預算,Meta的現金牛業務遭受重創。
面對危機,扎克伯格決定“用錢砸出一條路”:
在人才方面,不惜重金挖角,僅一個月就從OpenAI挖走七位核心研發人員;基礎設施層面,豪擲千億美元砸向算力,建設1GW的Prometheus和5GW的Hyperion超級集群,甚至自建200MW天然氣發電廠保障供電;商業化上,考慮放棄開源模型Behemoth,轉向閉源開發,以尋求更清晰的變現路徑。
從早期的技術領先、到ChatGPT時代的猶豫不決、再到如今的瘋狂追趕,多節點的接連落敗讓Meta陷入了一種被雙向擠壓的夾心層困境:向上,無法突破谷歌、微軟等老牌勁旅的技術壁壘;向下,被OpenAI、xAI等后來者趕超。
前有堵截,后有追兵的局面,讓昔日巨頭在這場AI時代的大戰顯中得愈發被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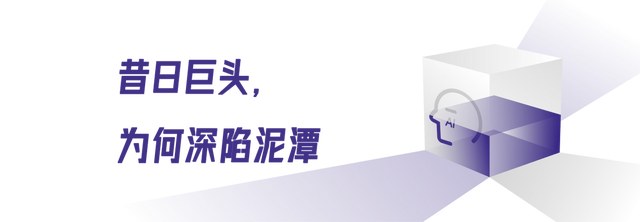
Meta在AI競賽中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,而是戰略誤判、技術債務和組織文化問題交織形成的系統性困境。這些因素相互強化,讓它一步錯、步步錯。
2021年,當其他科技巨頭開始布局生成式AI時,Meta卻全力押注元宇宙,更名并投入數百億美元建設虛擬世界。這一決策導致兩個嚴重后果:
首先,錯失生成式AI的黃金發展期,直到ChatGPT爆火后的2023年2月,Meta才如夢初醒般成立專門的生成式AI團隊,而此時OpenAI已領先一年。內部備忘錄顯示,OpenAI早在2022年就已采用H100,Meta直到2024年才開始大規模部署,嚴重拖慢模型開發進度。
其次,資源分散,元宇宙業務Reality Labs持續巨額虧損,2025年第一季度達42億美元,消耗了本可用于AI的現金流。當Meta終于轉向AI時,又面臨“既要追趕基礎研究,又要商業化落地”的雙重壓力,導致戰略焦點模糊。
近期,研究團隊的大洗牌更動搖了Meta一以貫之的開源立場,其苦心經營的開發者生態面臨流失困境。從社交媒體到元宇宙,再迅速轉向AI,Meta似乎一直在尋找下一個增長點,卻未能堅定執行任何一項長期戰略。
這種猶疑不決的態度在前期直接累積了嚴重的技術債務。
一方面,Meta將AI視為增量而非變量,一直沒有開辟獨立的商業化土壤,持續用于優化廣告等現有產品。短期商業回報的偏好帶來了一定收入,卻讓技術研發停滯不前、基礎設施落后。比如,Meta與竟對在算力上存在顯著差異。而即便現在投入130萬塊GPU建設1GW算力集群Prometheus,也需要時間消化吸收。競爭對手如xAI的Memphis集群已開始產出Grok4等成果,形成代際差距。
另一方面,重學術輕產品的特點阻礙了商業化。Meta每年在研究上投入數十億美元,產出數百篇頂會論文,卻沒有將其落地為用戶買單的商業產品,就好比只燒錢、不賺錢,在AI競賽中負重賽跑。
除了戰略和技術,組織文化的混亂特質也讓其難以形成穩定的技術路線。
內部人員爆料,Meta內斗嚴重化、技術路線割裂、搶功主義盛行,末位淘汰催生的恐怖情緒讓員工核心驅動力從技術創新異化為“避免被裁”,不少熱衷研究的核心人才離職。收購Scale AI后,外來精英與原有團隊產生摩擦,Alexandr Wang空降領導AI實驗室,砍掉多個學術項目引發老團隊不滿。政策上,Meta為頂尖人才提供的股權激勵多與短期股價掛鉤,可能鼓勵冒險行為而非扎實研究。
與硅谷傳統的使命驅動、OpenAI的AGI口號形成鮮明對比,Meta的AI戰略顯得功利而短視,更多是應對競爭而非引領創新。而這某種層面,也源于扎克伯格領導的一言堂風格。
可見,Meta其實已經危機四伏,即便加碼投入,也需要時間消化吸收。但同時,它的競爭對手還在加速前進。那么,深陷困境的Meta到底有沒有破局之路?如果有,在哪?

歷史表明,技術范式轉往往伴隨著科技巨頭的洗牌。社交媒體時代的Meta成功顛覆了傳統媒體,而現在,它又面臨著被AI新貴顛覆的困境。
但它的核心問題不在于資源匱乏,而在持續搖擺帶來的危機:既失去先發優勢、又缺乏后來者的靈活與專注。
如今,Meta正試圖用最野蠻的方式翻盤:砸錢、搶人、堆算力。短期內,它仍可依靠其規模優勢維持一定地位。但長遠來看,若不解決根本問題,很可能重蹈元宇宙的覆轍,巨額投入落空。
要扭轉局面,Meta需要的不只是金錢攻勢,而是從內部發力的幾個變化。
變化一:明確技術路線,放棄“既要又要”的搖擺策略,停止跟風式創新。
Meta在上半年的丑聞頻出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心態崩了,眼看著各家大模型以神速迭代,DeepSeek等AI新秀刷新榜單,研究團隊甚至不惜測試作弊向觀眾賣好。如今,Meta仍在開源與閉源之間猶豫,甚至可能放棄Behemoth模型。這種模糊立場或將引起更大爭議。想要翻盤,Meta必須明確技術路線:若堅持開源,則強化Llama生態,綁定PyTorch開發者,成為AI基礎設施提供商(類似Red Hat模式);若轉向閉源,則聚焦企業AI服務等高利潤場景,但需承受社區反彈風險。
變化二:注重技術的價值轉化,從論文導向轉向產品落地
Meta的AI研究長期偏學術,而競爭對手更注重工程化能力,需要設立“產品-研究”聯合團隊,打破傳統壁壘。研究流程上,借鑒谷歌Brain與DeepMind的融合模式,讓研究員參與產品設計,工程師介入模型優化,縮短從論文到產品的周期;產品上線后,利用Meta龐大的用戶行為數據(如20億日活社交互動)訓練模型,而非依賴純學術數據集;未來,超算集群等基礎設施應優先支持已確定商業化路徑的項目,而非僅滿足學術需求。
變化三:調整組織架構,避免扎克伯格一言堂。
Meta的決策過度依賴創始人,導致戰略頻繁轉向。下一步,公司要賦予AI實驗室更高自治權,類似Google DeepMind,讓團隊獨立運作,減少管理層干預。同時,優化人才激勵,建立長期績效體系,將高管薪酬與AI產品商業化掛鉤,而非短期股價波動。需要注意的是,團隊要吸取教訓,在AI、元宇宙、硬件之間明確優先級,避免資源分散。
而至于它究竟能不能挺過轉型陣痛,關鍵就在于接下來能否明確技術路線、保持戰略定力、重建工程文化。
當然,如果繼續自亂陣腳,Meta的AI黃昏或許將正式到來。

審核編輯 黃宇
-
AI
+關注
關注
88文章
35249瀏覽量
280459 -
Meta
+關注
關注
0文章
304瀏覽量
11878
發布評論請先 登錄
續航翻倍+3K錄制,Meta最新AI運動眼鏡亮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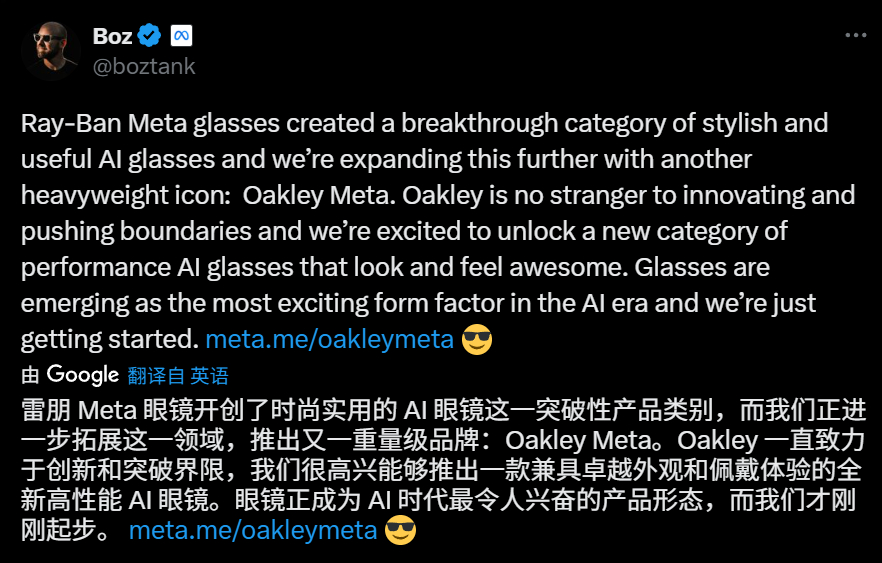
搶灘AI市場!Meta、NXP鎖定目標,2025又一重大并購來襲






 Meta的AI之路,為何節節敗退?
Meta的AI之路,為何節節敗退?












評論